中国新媒体(http://www.zhgxmt.cn):像上帝一样的人们
一、“都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从19世纪末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算起,时间旅行的故事在科幻作品中已不算稀奇。但20世纪中期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永恒的终结》中“永恒时空”的构想却意味深长——它是时间旅行的幻想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思辨性延伸,尽管它表面上只是科幻性的延伸。
简单说,“永恒时空”就是存在于在一年又一年、一步又一步的人类历史实践之外的一个超然时空。这个时空中的人们,不仅可以任意“降临”到人类不同的世纪(与“永恒时空”相对,它们被称为“一般时空”)之中,而且可以通过精确的观测和计算,以人们觉察不到的方式改变人类的历史路径。

你看,作者实际上构筑了“双重时空”,一个属于真实的人类,另一个属于虚构的“永恒之人”。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实际上也描述了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主体。其中一种,就是现实的人类;另外一种,则是通过科幻而虚构出来的超人类——“永恒之人”。
正是因为“永恒之人”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实际上是穿越千万个世纪)的观测、计算能力,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复杂的因果关联就具有超越凡人的认识能力。这种认识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因果之网中,准确地找到那个最终造成巨大结果的微小原因——仅仅对它采取行动。
比如,用小说中一个经典案例来说;“高级计算师亨利·威兹曼在那场后人耳熟能详的戏剧化事件中,移去了一位国会议员车上的刹车装置,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的发生。”
这种超凡的能力使“永恒之人”肩负着阻止大的灾难,保护人类生存的任务;尽管有时,他们也会用这种能力修正人类的生活方式。按照小说主人公哈伦的理解,“这都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而用哈伦的导师亚罗的话来说,一名时空技师“亲手引发的现实变革可能影响50亿人的命运。其中至少有上百万人的人生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以至于变成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新人”。
而在这种改变之后,历史上的一些人,可能就根本不会存在,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他们既可能是希特勒,也可能是莎士比亚。希特勒不存在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是莎士比亚呢?对,莎士比亚是因为别的必要变革而不存在的。为了那个更大的价值,莎士比亚又何足惜?在新的现实中。反正会有别的“比亚”出现。
显然,人类本身已经不是自己历史的主体。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崔正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崔正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http://img1.gtimg.com/ninja/1/2016/07/ninja146914950667835.jpg)
小说的主人公哈伦作为一位天才的“时空技师”,被“永恒时空”的最高权力机构“全时理事会”派往不同的时空分区,影响那里(那时)的现实;也会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私藏到111394世纪已经没有人类的未来时空。他的交通工具“时空壶”,就类似于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操纵杆上标示着到达不同世纪的精确刻度,只不过看起来设计(描写)得更为精密。
值得注意的还有“时空分区”的概念,它反映着“永恒时空”的管理体系, “永恒时空”把自己的观测师、计算师临时或长期地派驻于不同的世纪。这意味着人类过去与未来许多世代,都在“永恒时空”的管理之下。尽管7万世纪以上的“一般时空”是“永恒时空”不知为何进入不了的;而“永恒时空”产生的27世纪以前,则是无法改变的“原始世纪”,但“永恒时空没有尽头”,一直延伸到人类消失、太阳系消失的时代。
“永恒时空”中的住民“永恒之人”,是人类看不见的统治者。“永恒时空”的势力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大。因为它的疆域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置身于人类历史之外,又可以改变人类历史,这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在真实的人类历史时空之外的时空,难道不是天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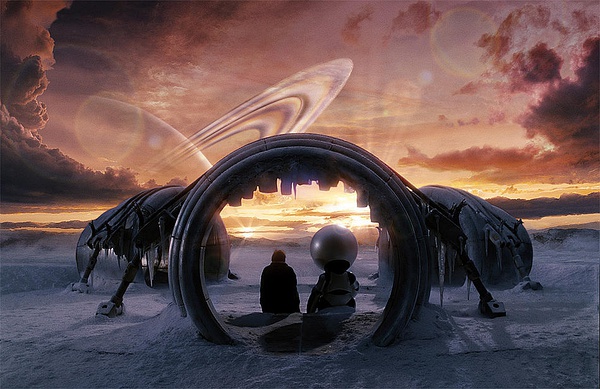
按照一个更好的价值标准改变社会现实——实际上是通过精细的计算改变人类历史。这正是“永恒时空”的使命。如果人类的每一个时代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办法彻底消除由于认识和能力的局限已经犯下的错误,那么人类的发展岂不是臻于完美吗?
这是“永恒时空”所体现的典型的乌托邦思维特征。
而作者对这种“改变人类历史”的实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视角,正是这部著作的“反乌托邦”特征。
严格说起来,只有表现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念及其实现,并且其中包含了历史上人们追求一个完美社会的社会空想特征,然后再以怀疑和批判的视角揭示这个理念和它实现之后存在的问题,它才可以说是“反乌托邦”的艺术营造。因此,如果只是在作品中表现了一个可能存在于未来的专制统治,那么它更适合另外一个称呼:“恶托邦”。在这个意义上,《永恒的终结》的“反乌托邦性”比20世纪更为著名的反乌托邦经典《一九八四》更为典型。
![[英]乔治·奥威尔/孙仲旭/上海三联书店/2009 [英]乔治·奥威尔/孙仲旭/上海三联书店/2009](http://img1.gtimg.com/ninja/1/2016/07/ninja146914984233203.jpg)
《一九八四》不过就是一个“恶托邦”。对于人类来说,它实在没有多少“可欲性”。所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才在《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一书中说:“20世纪著名的敌托邦小说都不是反乌托邦的。他们并没有像讽刺极权主义或者科技化的未来那样讽刺乌托邦的冒险事业。”
与《一九八四》相较,《永恒的终结》倒真的是在描写和讽刺一个“乌托邦的冒险事业”。
进入20世纪,传统的乌托邦写作式微,在相关学者的体系中,它已经成为扩展了的科幻小说类型体系的一个“子集”(a subset of the expanding genre of science fiction);也被看作科幻小说的“社会政治亚种”(sociopolitical subgenre of SF)。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科幻小说《永恒的终结》。因为它不仅仅写了科幻,也延续了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思考。
时间旅行的故事,较早典型地表现在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1895年发表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中。此前或同时代典型的社会空想小说(如《回顾》、《乌有乡消息》)的主人公大都是通过“做梦”到达人类未来的。威尔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则是驾驶着“时间机器”造访未来社会——公元802701年的。
但是,与此前或同时代典型的社会空想小说的主人公差不多,作为时间旅行者,威尔斯《时间机器》的主人公只是人类未来的纯粹观察者,尽管这种观察触动主人公和作者深沉地思考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性问题——社会发展到顶锋的人类退化问题。
然而,到了阿西莫夫1955年出版的《永恒的终结》,时间旅行的奇妙幻想竟然发展成改变历史和未来的壮志雄心;走进人类未来的观察者,也在半个世纪里进化成为一批人类历史的专业操纵者。
相对于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而言,阿西莫夫这部小说的创新(也包括批判性思考)之处,不在于时间旅行的科学幻想;也不在于对时间旅行的交通工具的更为细致的设计;或许,也不在于威尔斯没有想象到的“永恒时空”概念;而在于改变人类历史这样一种动机、效果和对它的反思:
在《永恒的终结》中,人类历史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主体,不是每一代在自己的认识条件和实践条件中摸索的人们,而是一小部分由人类各个时代遴选出来,选拔到“永恒时空”中的知识精英。
“现实并非一成不变、永恒存在,而是可以变来变去的,这个概念恐怕谁也不能面不改色地接受。”
但是,它不是我们许多人内心隐秘的希望吗?只是它与我们的生活理性太无法接通了,所以连我们自己都难以觉察。而阿西莫夫则借助科幻展示它,也反思它。
“永恒时空”的计算师们所设计出的“最小必要变革”,即使微小到没有人能够觉察出来,也使每一代人自己的任何历史实践都显得无足轻重。
比如,主人公哈伦作为时空观测师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482世纪。他觉得这个世纪毫无伦理道德可言,是一个被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主宰的年代,而且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体外孕育盛行的时代。所以,他就想对这个世纪设计一次现实变革——
“只要他对历史走向的扰动恰如其分地出现在某个关键点上,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在这种新的现实里,千百万原本只知道寻欢作乐的女人会变成真正的贤妻良母。她们完全生活在那个现实里,对现在这个现实里她们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无法想象,梦也梦不到。”
“但这是犯罪啊,永恒之人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是书中的女主角诺依脱口而出的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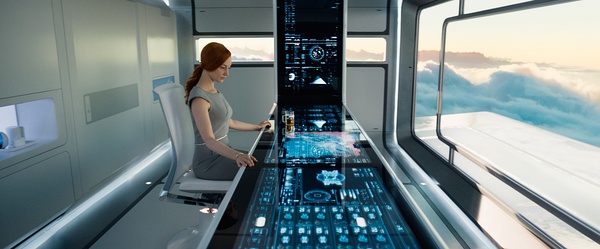
诺依是“永恒时空”在482世纪分区的“一般时空”里雇佣的一名普通人,也是进入“永恒时空”的唯一的女人。她与小说的主人公“永恒之人”哈伦堕入爱河。这场非法的爱恋,也最终葬送了“永恒时空”。
这场恋爱混杂着紧张、阴谋、决绝和毁灭的气息,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但是,作者把这位身世神秘的女人设计出来,也许只是为了提供一个批判的立场,一个批判的价值坐标。
正是通过这个女人,作者虽然肯定(假定)了“永恒时空”的可能性,却在价值层面上对它进行了否定。
然而,对这个美丽女人的神秘身世和她的神秘使命,我不能再继续透露了。一本精心构筑悬念的作品,毕竟不是为了让书评剧透的。这也是我和同学们在“乌托邦作品解读”课上相互分享这些作品时自觉遵守的规则。精彩的悬念本身就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它们应该留给直接的读者。而一篇书评的伦理底线,一方面是尊重作者的营造苦心;另一方面是不得破坏读者的阅读兴味。实际上,正是因为一位同学的课堂分享,才使我读了这本书,而他小心翼翼的分享一点也没破坏我的阅读兴趣。实际上,作者所设下的奇妙的悬念,不可能被概括性的叙述和分析点破。
三、无视个人的命运,却为整个人类操心在西方乌托邦作品研究的学术分类中,有所谓“空间乌托邦”与“时间乌托邦”之别。按照德国思想家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说法就是:
“人类的渴求所具有的形式,可以根据总的原则来陈述,而且在某些历史时期,愿望满足是通过投入时间来达到的,而在另一时期,它则通过投射于空间来进行。根据这种区分,可以把空间的愿望称作乌托邦,而把时间的愿望称作千禧年主义。”
这样的分类,也适用于空想小说的叙事结构。
《永恒的终结》作为以时间旅行为主要叙事框架的故事,似乎可以算作“时间乌托邦”。但它与传统的“时间乌托邦”小说有很大差别:
传统的“时间乌托邦”小说,往往也基于时间旅行的观念——比如,19世纪末美国人贝拉米的空想小说《回顾》,主人公一梦之间就从1887年进入了公元2000年。19世纪末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乌有乡之间》也大略如此。它们总是把完美的社会放置在未来。主人公虽然比他同时代的人们“提前”看到了美好未来,但是,未来的美好社会在逻辑上总是人类一代代追求奋斗的结果。
而在《永恒的终结》中,纵横于人类历史不同时代的“永恒之人”则是在“一般时空”之外,也就是在真正的人类历史之外。因此,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过去”,也没有真正的“未来”的。因为,在通常的意义上,“过去”,难道不是意味着再也不能改变吗?“未来”,难道不是意味着只有假以时日才能到达,或者因为人寿有限不可能到达吗?
更重要的是,因为“永恒时空”的存在,以及“永恒时空”对于人类社会和历史和干预,人类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对,我阅读这本书,常常感到作者有意忽略人类历史的这种实践性、积累性关系——通常看来,这是实在的历史因果。与其说作者完全不承认这种关系,不如说作者只是有意淡化这种关系。这是因为,对于这本书的主人公——在永恒时空中任意穿梭做时间旅行的“永恒之人”来说,人类代际之间的前后影响,不仅是意义不大的,而且是可以被他们任意改变的。
主人公哈伦在与他的学生谈到人类历史的时候,曾经轻蔑地说:
“一般时空里普通人教的历史都不管用,一次次现实变革早就把它们篡改得面目全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本身被描写得很渺小:
“他们只是一群可怜的牵线木偶,人形牵线木偶。他们永远都扬着小小的手臂,迈开小小的腿脚,以滑稽的姿式被定格在一般时空的某个瞬间里。”
在这本书的描写中,包括主人公在内的“永恒之人”都有轻视一般人类的性格倾向。这种性格倾向就是职业性的冷漠。因为,只要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改变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的话,那么,没有这样的职业冷漠是做不到的。他们对具体的人的命运完全无视,却在为整个人类的幸福操心。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时空旅行题材的科幻作品,具有明显的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人类所有世代都在一小撮精英知识分子的控制之下。而“控制”,正是反乌托邦作品所描写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无论这些未来社会是像《一九八四》那么严酷,还是像《美丽新世界》、《这完美的一天》那么“完美”。无论是为了你好,还是为了你坏。
我把这部科幻小说看作一部批判的书,它批判的正是试图通过科学技术改变包括人类错误在内的人类历史实践的理性迷信。他们有超级计算机阵列,“它们可以统合亿万种变量,计算出所有可能发生的现实,找到最优方案”。这种理性的迷信使一批“永恒之人”自己站到了上帝的位置上,尽管他们自己依然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肉身,虚荣、心计、权斗,一样也不少。
问题还在于,如果历史是变来变去的话,人类的历史经验便无从积累,人类也就不可能从自身的历史中获得认识的进步。实际上也就没有一代代延续的历史主体。
然而,也许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变来变去的历史”的质疑,作者有意为主人公注入了一种对“原始时代”的知识癖好:
“有时候他会迷失在那些古老的世界里,在那里人们生老病死、一切自然;在那里做出来的事覆水难收;在那里罪恶无法预防,幸福也无法规划,滑铁卢战役打输了,就真的作为败仗永留史册。有一首他喜欢的诗说道,亲手写下的字句,永远也不可能被抹去。”

这一段话耐人寻味,亚马逊的kindle上显示,有659人在自己的电子书中对它做了“标注”。它也使我想起《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在日记中悄悄写下的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是自由的、人们相互各异而且并非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事实存在不变、发生过就不会被清除的时代……向您致意!”
这两部小说主人公相似的心理,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不可改变性”对于我们的独特价值。被“真理部”篡改的历史和被“永恒之人”通过“最小必要变革”改变的历史,可能具有同样的性质。
而作为一个控制体制内部的反叛者,最终摧毁了“永恒时空”的时空技师哈伦,就是《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职员温斯顿。尽管他们两人的命运完全不同。
四、脆弱的逻辑和因果链条在今年7月旅行途中的一个下午,我在阅读此书时忽然想到用一句话来概括对这本书的感受,那就是:“把时间看作空间。”对,这正是这本书的描述常常传递给我的感受。表面上看,“把时间看作空间”正是“时间旅行”这个修辞化表达的自然延伸,但在“永恒时空”的具体呈现中却不免显出悖谬荒诞之处。
比如,主人公哈伦作为时空观测师被派到482世纪所写的一份观测报告中写道:
“482世纪迫切地想向其他一些森林过度砍伐的世纪(比如1174世纪)出口更多的纤维纺织品,却不愿意只换回一些熏鱼。”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把482世纪和1174世纪分别看作一个“地方”,比如美国和中国,那么这一句话很正常,它反映的不过是人类的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换和普遍的相互依存。但是,如果你按照词语的本意把482世纪和1174世纪理解为前后相隔甚远的不同时代,你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句荒诞不经的话。482世纪的时候,1174世纪还不存在。1174世纪的时候,482世纪已经没有了。
而且,从人类对历史实践及其影响的角度来看,1174世纪不正是482世纪的结果吗?两者之间怎么能够进行交易呢?
但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我感觉,这是作者有意的荒诞化写作。通过这样的写作,考验读者的实践理性;并通过这样的实践理性向读者暗示“永恒时空”在逻辑上的脆弱。
“永恒时空”的价值基础,其实也是脆弱的。就以其通过精确的观测计算改变人类历史的所谓“最小必要变革”理论而言——比如,主人公哈伦作为时空技师第一次执行的变革任务:
“他在223世纪花了几分钟时间,做了一点机械上的小手脚(堵死了一辆车上的离合器),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年轻人错过一节本该去上的机械工程课,然后他一生都没有进入太阳能发动机领域,然后一个简单而完美的小设备的发明时间就被推迟了整整十年。最终的结果非常美妙,一场224世纪的战争从新的现实中消失了。”
这样的变革如果在逻辑上能够成立,你就必须假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真是这样的单一因果。
历史事件的叙事法往往会突出某个具体事件的重要影响——比如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枪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只是叙事法,而不是历史复杂因果。如果真的认为历史是这样的单一因果的话,那么,按“永恒时空”的操作方法,需要做出的“最小必要变革”,就是完全取消普林西普的父母作为青年男女见面的机会——因为两个青年男女认识的机会可能完全偶然,因此就根本不会有普林西普这个人。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被从历史上抹去了。
但实际上,正如世界大战是多因的一样,人类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是多因的,尽管普林西普出生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他的父母有机会恋爱,我们所有人也是这样。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写道:
“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生,引用一件轶闻奇事作为广泛而深刻的事件的第一原因,这在历史上已经成了常见的笑话。这样一个所谓的原因,看来不过是一种机缘……”
这种类似于“一个马蹄钉输掉一场战争”的单一的因果链条在互联网上已经演绎出许多类似于“滑坡谬误”的有趣段子,比如,从“假如潘金莲不开窗户”一直推导出“中国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再比如,从“若当时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经过10步推出“因此到今天,中国将是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远远领先于日本、欧洲、美洲”——不一而足。
因此,“永恒时空”通过“最小必要变革”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在逻辑上其实是不成立的。阿西莫夫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以这种藏着漏洞的单一因果逻辑虚构出“永恒时空”,也许只是用来对它存在的价值进行反思和批判的。

“永恒时空”的脆弱,还体现在作者有意为它的存在制造了一个“合不上”的因果链环:24世纪的科学家马兰松发明了时间力场;3个世纪之后,“永恒时空”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马兰松却又不可能发明时间力场,因为时间力场的数学理论基础“列斐伏尔方程”要到27世纪才问世。所以,“永恒时空”居然需要把一个人派到24世纪去教会马兰松学习“列斐伏尔方程”,以使“永恒时空”获得自己存在的基础。
晕了。马兰松到底有没有发明时间力场?如果没有,“永恒时空”又因何存在?如果发明了,永恒时空又为什么需要派人教会马兰松自己根本不知道的知识?谁在前?谁在后?谁是因?谁是果?
阿西莫夫就这样把“永恒时空”置于细若游丝、若有若无的因果之链上。
五、回到人间“永恒时空”,一个可以任意改变人类现实和历史的时空。尽管它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时空,但是,活在世上的一些人,他们的内心也许渴望拥有这样一个位置,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他们便愿意拥有它。
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现实性。它对应着可能永远发生的乌托邦冲动。这部科幻小说的批判性,它的反乌托邦性,就在这里。
而在小说中,这些批判是通过主人公哈伦的内心觉醒,尤其是通过美丽女人诺依与她深爱的男人哈伦的对话来展现的。这些对话肯定了人类每一代人自主决定命运的权利;肯定了人类发展的多样性价值,比传统乌托邦作品中的对话更深刻,而比一般科幻作品有更多的思辨性和批判性。
比如,诺依说:
“在消弭人类灾难痛苦的同时,永恒时空也消除了人类走向辉煌的可能,只有经过严酷的考验,人类才能不断前进,走向发展的可能。危机的环境和危机感,才是驱使人类不断进步,不断征服新事物的根本动力。……”
在这句话中,阿西莫夫实际上接续了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对人类社会发展终极问题的思考:即失去发展目标之后的人类退化,平庸地存续,还是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同时也意味着新的艰难困苦),以持续发展。
“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浮士德》)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使男人觉醒。就像著名反乌托邦作品《一九八四》中的茱利娅之于主人公温斯顿,《这完美的一天》中的丁香之于主人公奇普,《永恒的终结》中的美丽知性的女人诺依也把主人公哈伦引上了一条觉醒之路,并把他从“天上”带回人间,带回“永恒时空”不能改变的世纪和普通人的生活中。就像七仙女下凡人间和董永一起过日子一样,泯然众人。与那种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地位相比,作者难道是在肯定普通人的生活价值吗?
最后,我应该说,反乌托邦,只是我对这部科幻小说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在书中有确实的根据。但阿西莫夫之所以否定“永恒的时空”,其实还有另外的价值标准和事实判断,比如人类应当迈向太空什么的——“永恒的时空”阻碍了这个伟大目标,使人类困于地球。不知是真是假。限于目光短浅,我对这个理由不予置评。

参考文献: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永恒的终结》,崔正南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明、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A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Edited by David See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英]奥威尔《一九八四》,孙仲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美]艾米拉·莱文《这完美的一天》,吴建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